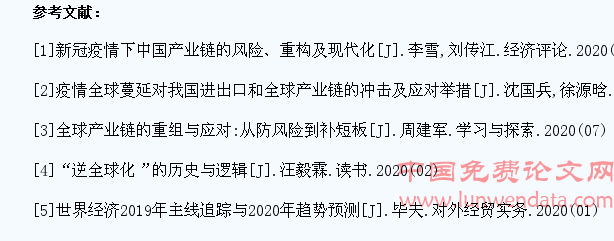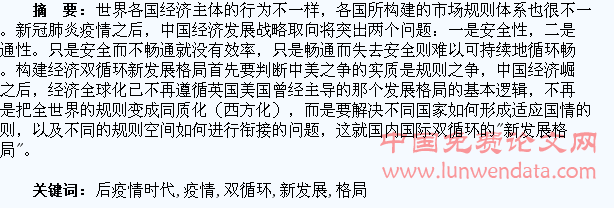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进步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进步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新进步格局是经济进步的客观趋势,也体现了策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是规则博弈的纵深化。这是在中国经济进步进入新年代,基于对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所做出的策略判断和方向引导,以此开启中国经济进步新征途。
1、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济进步的客观趋势
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进步态势,其实是大国经济进步的一个趋势性事实。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较封闭的进步模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体系,进出口比重非常低,国际资本极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开始进步国际大循环,发展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越了GDP的增长率,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到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到2006年前后已经开始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贸进出口遭到了非常大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6%以上,一直降低到2019年的17%左右。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低到2019年的35.7%。常常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2007年的10%左右降低到2019年的1%左右,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经验性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的进步道路,经济进步比较快的国家也都实行较自由的市场经济。根据主流经济学思维范式,市场经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具备增长的无限性。增长的无限性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由于工具理性所追求的不是用价值而是交换价格。交换价值以货币形态来表现,企业追求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价值最大化。世界各国由市场经济主导,无限地追求交换价值,其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就势必是经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具备扩展至全球的内在冲动。那样,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势必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进步,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
就某一国家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比重,第一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小国经济的增长更大多数要进入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循环。比如,新加坡的国际经济循环部分就很大。而大国的国内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通常来讲国内循环的回旋空间大,有更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国内市场中完成循环。比如,美国尽管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庞大的国内经济,它的国际经济比重就相对较小。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7%左右,而美国这一比重还不到10%,尽管它的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比中国更大。第二,在经济进步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双循环格局也有密切关系。各类产业的商品可以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两类。农商品譬如粮食、玉米、大豆等大宗产品是可贸易商品,矿产、石油等资源性商品,是可贸易性非常强的商品,工业制成品也是可贸易性较强的商品。而另一类经济活动或其成就(商品)的可贸易性就较小,比如房子、电力等,大多数是国内消费,只有极少量会售出到海外。伴随经济的不断进步,不可贸易商品的增长加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一般会提升,不可贸易商品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中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境外,形成服务贸易,但和制造业、农业相比,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一般比较小。所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国民经济中的可贸易商品比重一般会降低,不可贸易商品比重上升。最后,影响国内国际市场比重的一个要紧原因就是经济学特别关注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及其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关系,与各国间的资源差异所致使的国际分工情况。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遭到国际分工的深刻影响,反之,国际分工的深化也使得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愈加融合。
假如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一个趋势性事实。所以,今天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并非需不需要双循环,而是要形成新进步格局。要认识“新”在哪儿?目前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进步格局,含义是深刻的,不止是指出一个经验事实或趋势性事实,而且具备重大策略意义。
2、新进步格局体现了策略关切取向的调整
经济学和经济进步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关切分别是效率和公平。经济学的第一个要紧关切点是效率。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可以达成高效率。只须允许自由角逐,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用途,它就能(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因而效率非常自然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关切点。经济学的第二个要紧关切点是公平。但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总是不可以让人认可地解决公平问题。公平分为事前的公平和事后的公平。事前的公平主如果指市场秩序(产业组织)是不是能保证公平角逐;事后的公平主如果指市场角逐所致使的结果是否公平,也就是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是不是均等。当然,经济学和经济进步还有一些其他的关切原因,譬如不确定性原因、风险性原因等,但对这类问题的关注也大多归结到效率。而当考虑到国际关系时,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循环时的两个主要关注点,即各国间的市场是不是存在贸易壁垒,是不是存在关税。因而国际自由角逐的经济学逻辑,就是没贸易壁垒和低关税,最好是零关税、零壁垒,那样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就能一体化。假如达到零关税、零壁垒,国际和国内循环也就没什么不同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本逻辑。
从根本的理论逻辑来讲,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进步格局,就是在原有些理论逻辑中加入一个要紧的关切原因:安全。也就是说,当强调新进步格局时,事实上体现了策略关切取向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中也有安全原因,主如果指财产安全和人权保障,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人身独立的“经济人”,都追求我们的利益,不受威胁,私人财产得到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假定,是一个规范首要条件,没安全就没市场经济。但这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目前的世界发生了非常大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安全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对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越了效率和公平。在很多状况下,宁愿牺牲效率和公平,也要保证安全。于是,安全成为经济思维和策略取向中的一个特别要紧的关切原因,但安全非常难概念。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安全是经济主体的安全,尤其是财产安全。而企业层面的安全是供应求购关系的安全。从需要来看,生产出的东西能否卖得出去,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假如有了障碍卖不出去,就是需要环节的安全风险。而从供给来看,假如发生产业链、Supply chain断裂的状况,比如所需要的“卡脖子”技术没办法获得,就是供给环节的安全风险。供应求购关系的安全性是经济安全。除去经济安全,还有其他多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秩序安全等。当经济全球化愈加进步,安全问题也愈加国际化,表现为诸如疫情国际化、恐怖组织和活动国际化,这类都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副商品”。再进一步是更复杂、更难概念的国家安全。而且每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概念很不同,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政府治理体系可能非常不相同,或各具特点。正是因为对于安全关切的提高,使得新进步格局体现了策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换句话说,因为对安全的深度关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需要形成更具安全关切性的新进步格局,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进步策略的要紧内容。
3、国内循环为主体以规则博弈
纵深化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得新进步格局的双循环态势,尤其是对于大国而言,应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作为基础。这是由当今世界正在展开和不断深化的规则博弈变局所决定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第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即假定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表现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第二是空间的匀质的,好似空盒子一般,经济主体和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想象的经济空间中进行互动。假如根据如此的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思维来想象经济全球化,那样各国都门户开放,各国的企业都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行为目的,普通的企业均为私有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自由角逐,最佳的是零关税、零壁垒,就能达成最高的经济效率和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坚信这一经济学传统范式的人觉得,假如现实世界离开了这个想象中的经济全球化格局,那就不合理了。但现实世界恰恰很不同于经济学传统范式所想象的世界。世界各国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同,各国所构建的市场规则体系也非常不同。放眼世界,当暴发新冠疫情后,为何每个国家应付疫情的方法各不相同呢?中国的抗疫成效非常不错,而其他国家不可以实行是什么原因就是,各国的价值理念不同,对于安全的概念不同,政策目的的优先顺序不同,所采取的抗疫方法当然很难相同。根据如此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双循环新进步格局,可以看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第一,经济主体(企业)的性质和行为目的并非一样的。中国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特别是金融业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要紧产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的跟民营企业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二,规则空间不同,我的办法对我非常合适,但对你可能不合适。这就是现实的世界。所以,提出双循环新进步格局,事实上暗含着如此的学理考虑: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规则空间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不同的规则空间中,什么空间愈加有效率,愈加安全,各国企业就会倾向于到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地方去进行经营活动。目前大家愈加倾向于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今天的世界,至少是在相当一部分范围中,国内的规则空间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要比国际的规则空间要更好一些。也可以反过来讲,在国际规则空间,企业经营的安全保障可能不如国内。所以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可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性。每个国家在关切安全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大国,都会考虑如何把跟自己国家经济命脉有关的要紧环节掌控在自己手里。当然,这并非说要舍弃国际循环,而是要考虑到产业供应求购关系的安全性,期望在国内构建愈加完整安全和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因此,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进步策略取向将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性,另一个是畅通性。只不过安全而不畅通就没效率,只不过畅通而失去安全则很难可持续地循环畅通。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文化和历史不同,价值观不同,社会偏好不同,所以应付安全性和畅通性的关系势必有不一样的国情特点。那样,构建经济双循环新进步格局有几个重点问题。第一要判断中美之争的实质。中美冲突根本上是规则之争,美国人觉得他们那套规则是唯一适当的,基于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承诺,具备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在那个范式承诺下所构建的经济学和经济规范,是唯一最佳的。假如离开那个经济学范式,就是不对的异类。美国人目前就是坚持这个思维框架,因而觉得世界上没第二种经济科学,也没第二种有效规则体系。但,如前所述,这种范式框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实,连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承认,在人类经济进步的版图中存在着“另外的世界”,而且可以获得不次于美国的进步效果。在20世纪之前,因为没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步成功案例,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昭示世界,人类社会现代化确实还有其他的成功经验和可行道路。在这个“另外的世界”,不同于西方化,也可以达成非常高的进步效率,其公平性和安全性与西方化相比,也不差。深刻的考虑可以揭示,世界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动摇,关切点发生了改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主体和空间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已经不是现实的图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经济全球化已不再遵循英国美国过去主导的那个进步格局的基本逻辑,不再是把全世界的规则变成同质化(西方化),而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怎么样形成适应国情的规则,与不一样的规则空间怎么样进行衔接的问题,这就是“新进步格局”。目前大伙都在说世界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子就是规则博弈和规则重塑。因为现实世界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认定的全球规则一元化世界,而是一个域观世界,即世界经济是以不同域态域境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主权国家拥有规则安排的主导权。以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逻辑来看,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体现了中国规范性质和价值文化特点,可以适应中国国情。当中国经济大规模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当然会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形成规则博弈之势。
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规则博弈表现为破坏性过程,拜登上台将来,可能表现得较具建设性。所谓建设性,就是以对话谈判方法进行规则博弈。其实这对中国的重压并不会更小。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发生要紧变化的过程中,即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进步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因为中国经济进步的策略取向势必地将愈加突出安全性和畅通性,所以各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怎么样既要承认各国规范规则的域观性,即“特点”和安全关切,又要达成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将成为构建新进步格局过程中的艰难经历。尤其是,当大家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时,事实上意味着一系列规则安排和政策设计的预想。比如,采取国家补贴方法促进国产化、以举国体制克服“卡脖子”技术等,都要体现为具体的规则和政策,这类规则和政策能否有效?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妨碍国际角逐的公平性?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进步格局,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考卷。